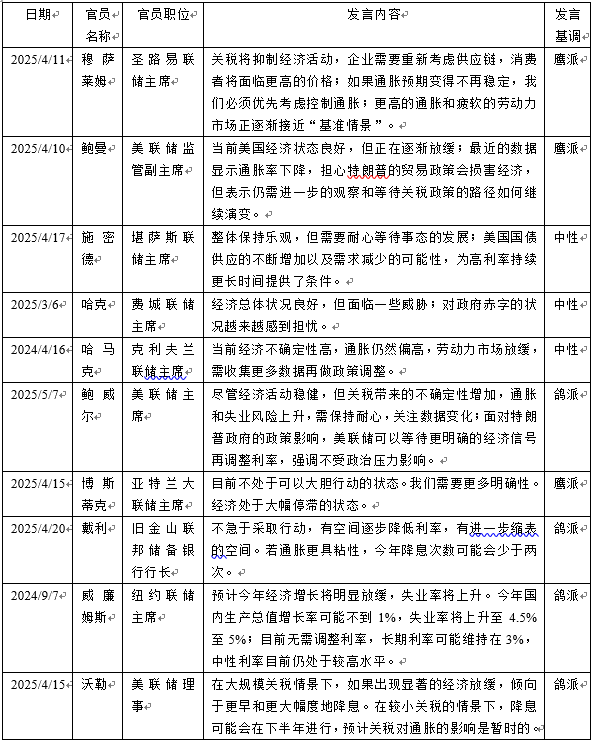“1947年7月的午后,主席,能不能同我们合张影?”高智鼓起勇气脱口而出。 毛泽东抬头专业股票配资炒股,手里的铅笔只剩光秃秃的木杆,他笑着反问:“照片?你们可别嫌我忙啊。”一个俏皮的眼神,让在场的同志们都松了口气。
这件“小事”发生在靖边县小河村。那一年,胡宗南的部队刚把延安“推平”,中央机关不得不分散转移。旅途艰辛,吃住简陋,胶卷更是紧俏,照相机常年锁在木箱里。正因如此,工作人员才把一次合影视为难得的“奢侈品”。
高智想拍照的念头并非一时兴起。他是机要室里年纪最小的报务员,干的是抄电和译电的细活,平常只能透过窗缝瞧见主席忙碌的身影。能留下同框照片,对他来说既是荣耀也是纪念。只是,他不知道如何开口,直到借铅笔事件给了他灵感。

那天上午,毛泽东需要一支新铅笔修改作战要点,秘书叶子龙跑遍了几个部门,才在机要室借到二十多支“施德楼”。同事们没想到主席会缺铅笔,更没想到自己随手递出去的笔会触发一次合影。高智抓住时机,用陕西口音嘀咕了一句“要不就一起照个相”,便把自己推到前台。
毛泽东性格爽朗,见大家拘谨,故意打趣:“给我这么多铅笔,不就该回礼吗?走——照相去!”一句话点燃了众人热情。几乎瞬间,机要室、秘书室和警卫班的同志一窝蜂挤到院子里,搬板凳、擦镜头、调整感光度,一通忙活。摄影师焦急地挥手:“别动,站稳,底片只够拍三次。”
构图排位是一门学问。李质忠处长指挥:“个子矮的蹲前排,个子高的站后排,中间留给主席。”高智个头不高,理应占据前排C位,可他临拍摄前还是让出半步,把身子侧在主席右前侧。咔嚓两声过后,胶卷已空。拍摄完成的那一刻,大家像打了胜仗一样,七嘴八舌围着摄影机——只有高智低着头,心里忐忑。
几天后,洗出的样片送到叶子龙手上。前两张尚可,第三张却让高智差点掉眼泪:他的脸被半截肩膀挡住,只剩右脸贴着照片边缘,他忍不住嘟哝:“老叶,这可咋办?只剩半张脸,回家咋跟母亲说?”叶子龙一时语塞,偷偷拿给主席看。

毛泽东盯着那张“半脸照”笑了:“小高自己挪的位置,怪不得人家相机。”话虽如此,他还是让后勤再找胶卷。然而转战在即,没有多余物资,第二次合影只能作罢。高智只好把那张“残缺”的相片包好,塞进电报册里随身带着。
战事推进,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打出声势,中央机关逐步北移。1952年,高智因表现出色,被叶子龙推荐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局,真正成了毛主席身边的秘书。十年的日夜相伴,他见证了《论十大关系》的创稿,也目睹主席凌晨批阅文件的专注。每逢闲谈,主席偶尔调侃:“小高,当年那半张脸,现在怕是值一箱铅笔了吧?”一句轻松的玩笑,夹杂着老友之间的默契。
进入60年代,国家建设全面铺开,毛泽东屡次嘱咐警卫、秘书到地方锻炼。高智恋恋不舍,申请回陕西,带着那张旧照片和满脑子工作经验,成为省里的一名干部。离开北京后,他隔三差五写信向主席汇报,不谈官职,只聊天气农事。1976年9月,他在西安听到噩耗,整夜伏案,唯独把那张半脸合影摆在灯下,烟灰落满桌面,也没挪动一下。

20世纪末,李敏主编《毛主席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》时,多方搜集史料。高智珍藏的相片被影印进书里,出现了三次——一次大图,两次局部。出版座谈会上,有人指着模糊的侧面笑问:“这半个人是谁?”时任陕西某地级市老干部局顾问的高智抿嘴,只说:“年轻时不懂事,站错了位置。”一句平常话,让很多老同事红了眼眶。
今天翻检档案,这张相片依旧存放在中央档案馆的恒温柜。影像里,主席身着灰布军装,神态轻松;左右两侧的工作人员有的满脸稚气,有的略显疲惫。右下角半截脸的高智像是向外探出,仿佛在对后来人诉说什么——胶卷有限,机会难得,时代在推着每个人前进,你若错过取景框,就只能留下遗憾。可正是这份遗憾,让一位基层报务员在回忆中保留了最鲜活的瞬间,也让后人看见了战争年代“普通人”的真实表情。
影像定格,历史不停。高智那半张脸,承载的不仅是一段插曲,更是战火岁月中人与人最朴素的信任与惦念。
新宝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